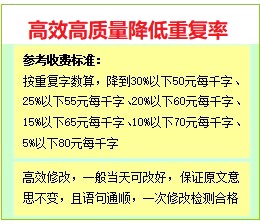何为侠者?古代的游侠仅凭意气,任意攻杀,或仅凭交情,不问是非曲直,以睚眦杀人,事实上这是对侠义原则的肆意践踏,只是将现实中的流氓习气夸大地搬到小说中来。然而,武侠小说中称得上“侠行”的,并不是那些贩夫走卒偶尔怒发冲冠的冲动之举,而是那些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大善大美、至情至性、至尊至极的人。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推崇的侠士风范正是至情至性,独立自由。如令狐冲不是大侠,但他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再如曲洋是魔教长老,但他能为知己而死,也算至情至性,虽说没有侠名却有侠风。尽情挥洒恣意率真的本性,决无半点做作掩饰,也绝不管世人的褒贬毁誉的超脱与放达,这就是《笑傲江湖》所要塑造的侠。他们视权力如粪土,视钱财如浮云,在与丑恶人性的对比中生出光辉来。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提及到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笑傲江湖》中一些人物虽然有着政治人物的特点,但小说着力表现地不是政治,而是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如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表现。贪、嗔、痴等种种人性的向阳向阴面,金庸都通过人物刻画出来,可谓是百态人生。《笑傲江湖》中金庸着墨最多人莫过于岳不群这类人与令狐冲这类人。这两类人的不同,形成的强烈的对比,可以说金庸是有意地将人性的中的欲念与冲淡进行对比。他通过岳不群、左冷禅之流对权力汲汲渴求,最终不得善终的刻画,表达了对人性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他选择了拒绝名利、不为物累的魏晋风度来反射人性的自由。小说隐晦地道出了人世间的是非争夺,利害得失是无法消除的现实,惟有心灵的超越才能不为其所动,才能超然物外,自在逍遥。
(三)与“越”地域文化有关
为什么说金庸写魏晋风度与越地文化有关呢?魏晋风度是一种反常风度,它具有一定的反叛性而越地文化也同样具有反叛性格,在这点上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越文化源远流长,谈到越地精神,人们通常用“胆剑精神”来概括。胆剑这一典故来自勾践兴国的故事,“胆”有铭记苦难和坚持持久之意,“剑”则有进击和反叛之意。《笑傲江湖》中表现的最为深刻的就是不苟陈规的批判精神和不同流合污的叛逆态度了,在这点上,笔者尝试从越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金庸的创作。越地自古以来,便多慷慨之士、多狂勃之徒、多反叛之人。这种反叛精神则在越文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形态,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来:
蔑视权贵,崇尚气节。如魏晋名士嵇康,《世说新语》中有第二十四则对嵇康敢于得罪权贵的记载:“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具佐鼓排。康扬锤不缀,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5](p24)这段掌故,成了嵇康断送了性命的催化剂。然而,嵇康在为自己潇洒恣意的行为买单时,并没有后悔,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曾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嵇康一介书生,铁骨铮铮,不惧赴死,宁保人格,堪称典范。
敢倡异端,独标新说。如东汉王充,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用充分的说理,横扫东汉最高统治者所迷醉的谶纬神学。他坚决反对国家意识形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认为国家的兴衰和天象关系,全是人治造成的。更为大胆的是,他还将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礼教说“礼者,忠信之薄也,乱之首也。”这点与嵇康反抗“既成礼法”堪称伯仲。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竟然敢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还有浙东学派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站在“公天下”的视野之下,猛烈抨击“家天下”的意识。他利用人性和道德的观点解释君主的起源和实质,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神化君主,神化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扫除了“君权神授”的神圣光圈。
救国救民,革命到底。越地多爱国之士,为国昌盛,出谋划策,不畏革命之艰。巾帼亦不让须眉也,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鉴湖女侠秋瑾。她虽是弱女子,却敢于冲出封建的藩篱,只身去日本留学,寻找救国之路。回国后,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后为人告密,慷慨赴死。同为越籍人士的鲁迅也把越文化的“胆剑精神”表达地酣畅淋漓。他完全认同越王勾践的叛逆精神,声称“自为越人,未忘斯义”。事实上,他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他是古越“胆剑精神”的优秀传承人。
越地的反叛精神一直都没有消亡,它始终存在于越地域的文化之中。《越绝书·记地传》记载,孔子往见越王,说:“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答曰:“夫越性脆且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而越地的这种民风,有利于非正统,反独尊的思想的形成,并进一步成为孕育异端思想,反传统礼俗精神之土的沃土。无论是“疏放不为儒缚”的徐渭还是故作滑稽、玩世不恭的王思任抑或是适情任性、时涉诙谐的张岱,无一不冲破自己的文体,束缚保有自己的个性。越文化的反叛性可见一斑,越地的名人也或多或少地有着卓异、桀骜、旷达、豪放、怪诞、高雅、浪漫的特点。
金庸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必然会有一些反叛精神,而这一反叛精神也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最具特色的一点便是反抗精神。“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句话可以说是切中肯綮,十分到位了。侠客通过武力来反抗社会现行的规则,他们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反叛者。人们对侠行津津乐道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这些具有超人格魅力的侠客来向那些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权威进行挑战,以“侠义道”来解构大一统的专制文化传统。除了普通民众对侠津津乐道外,文人们对侠更是向往,要不怎么会有“千古文人侠客梦”的说辞呢。当然金庸也有这样一个侠客梦。然而,侠作为一个群体,它并不是同一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侠的类型可谓是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金庸写的侠客类型也很多,而《笑傲江湖》中表现的侠的类型则是名士型侠客。这种名士的狂荡是建立在至情至性上的狂傲——睥睨一切,独往独来,任情恣慾,率性而为。它更易为社会所接纳,更符合文人的胃口。令狐冲追求的笑傲江湖正是此等独立苍茫,傲视千古,注重个人意志,追求个性舒展,不愿为世俗人生的种种准则规范所束缚的人生。他的这种追求,与越地文人性格中的反抗性有相一致的地方。他的个性则与魏晋名士有着承继的关系,它们都有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一面。而这种承继关系同样体现在魏晋风度与越地文化上。
浅谈金庸《笑傲江湖》中的魏晋风度(三)由毕业论文网(www.huoyuandh.com)会员上传。